
《床 / 自然系列 No. 10 》, 1993 ,烧焦铜丝、丝、茧 800 × 200 × 10cm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藏,艺术家与香格纳画廊供图
每每蚕开始吐丝,就会迎来 5 个不眠不休的夜晚,为了观察蚕吐丝的过程,艺术家梁绍基常在工作室席地而卧,一日半夜醒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肩、颈、头之间已经被掉落的蚕悄悄地用蚕丝连接起来。他突然醒悟, “疲于奔命的我,岂不是一条蚕吗?”
现年 76 岁的艺术家梁绍基自 1989 年开始养蚕实验,至今已逾 30 年,对他而言,蚕既是创作媒介,又是在一种天人合一的创作方法中亲密互动的伙伴。在不断熟悉和研究蚕的行为学、基因学、蚕业人文史的过程中,他从微观世界里认知宇宙、自然、科学、社会和历史。
海德格尔说,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为了追寻唐朝诗僧寒山的生活踪迹,梁绍基将工作室搬至天台并生活于此 20 余年,天台山坐落在浙江天台县内,这里有中国佛教天台宗和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 — 国清寺。从前只有大巴相通,直至近年才有高铁与上海相通,佛宗道源,山水神秀是对这里最好的形容。在梁绍基看来,这里显然与都市节奏慢了几个节拍,因此他在大城市中接受新鲜信息之后,退回到天台自己消化。他在创作中与自然亲近,自 1989 年开启的“自然系列”是艺术家与蚕之缘的伊始,他曾经在创作札记中写道在“养蚕实验中,我发现蚕所吐的圈圈丝迹似云弥漫的形态,遂感悟到云时自然、生命、历史的呼吸,是一种变幻万端永恒的运动”。
炼狱、通道、天庭、命运、白光
生命体的必经之路
9 月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的梁绍基大型个展“蚕我,我蚕”除了系统性地梳理了“自然系列”之外,也回望了其创作脉络中各个重要阶段的代表作。展览被艺术家分为炼狱、通道、天庭、命运、白光的线索,观众进入展厅后首先经历的是炼狱,地上摆放着扭曲的链条,就像地狱里生长出来的腰蛇一般扭动,象征着重量和力量感的链条、钢铁被蚕丝缠绕、包裹,柔与刚的共存和对抗共同向上,指向空中。钢铁的锈是艺术家很喜欢的自然现象,他觉得这种惨败都是一种对时间的描述,废墟背后饱含故事。
古香樟木、蚕丝、蚕茧构成了“沉云”系列作品,从一层蔓延至楼梯,缓缓上升,通过蚕的通道,就像蚕在蠕动一般进入二层的“天庭”,万物皆有灵,皆可沟通,是梁绍基看待万物的视角。这些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被锯掉的树根,就是我们目前对待传统的现状,展览中所用的木头是来自唐朝的古木,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在中国山水画中,云聚集的地方被称为“云根”,而一些圣人居住的山坳里面也叫“云根”。
随着蚕道上至“天庭”,观众也可以开始用蚕的眼光来观看一切。由蚕道入天庭,天、地、人这三个来自中国哲学的要素均有出现, “我再输入神性的因素,就变成了海德格尔以及中国所有宗教里面都涉及的宏大主题:天地神人”。 这不仅暗喻着生命体发展、轮回的过程,也同样隐喻着对人性、对社会的观照,以及对宗教的解读。
曾经在北京木木美术馆展出的《天庭》此次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变成了一个 10 米高、 30 米长、 11.8 米宽的大装置,梁绍基认为作品需要有人走进去,因此空间感很重要,外部的蚕茧形状则是映射着“一蚕一世界,一茧一宇宙”的蕴意。四个三角锥体依次排列,这是艺术家自 1992年开始用的艺术语言,如果把三角锥体倒置,变成与沙漏一样的造型,暗示着时间的概念。 《天庭》的深处,是三个光柱,西方有三圣,即圣母、圣子以及圣灵,而东方亦有三圣,寺庙中也有三圣,在这里不言而喻。他坦言在创作这件作品时,糅合了他对神、人、社会、宗教理想,以及对那些所谓的社会末端人士的生活状态进行反思,对大家都在思考的“梦天堂”提出疑问。
2020 年,一切归零,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 · 弗里德曼认为人类将会以新元前和新元后作为书写世界史的分水岭,梁绍基在札记中写道, “庚子年是令人百感交集的一年,而‘ 0 ’则是时间的钟摆, ‘ 0 ’的中部充满虚空、虚静,构建了一个自省的空间,暗示着人们在疫后要学会反思、敬畏自然、克服妄欲,艺术家则应该从艺术的庙会、秀场撤退,认知艺术的真正任务和担当。”
由“物”转“道”
对生命的观照,对艺术的追求
海德格尔曾经提出“存在者”的概念,一条蚕丝的存在,其实也映射着每一个人在世上存在的蛛丝马迹,蚕丝存在的状态,就是它的本身,在以蚕丝为媒介的创作中,总是蕴含着生命的特征。在尝试过多种材料、媒介创作之后,他最终选择忠于“蚕”这一物,并用蚕丝连接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
通读中西方哲学的梁绍基认为中国和西方自古至今有许多对话,而薄薄的、虚透的蚕丝,有着东方的、诗意的美。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他关心的最本质问题,是观照生命和观照世界。他多次提及自己非常喜欢禅宗,喜欢老庄的哲学,以修身为核心,老庄对生命的态度、对宇宙的态度在梁绍基看来是许多其他中国哲学家不能企及的。而养蚕的过程,便是修禅的过程,在夜晚听蚕的时候,必须沉下心,才可能读它,领悟它。
在创作“床 / 自然系列”的过程中,艺术家最初所创作的床均是长十余厘米的小床,后来经朋友鼓励想尝试更大尺寸,他购入了两个婴儿床,然而当把蚕放上去吐丝时,他发现不对,这是作秀,因此作罢,回归至小床。 “唯独只有自己也用蚕的情感去观照世界时,才可以感同身受。”对于蚕而言,十几厘米的小床,才是它们所存在的世界,这个小床是艺术家与蚕贴心的通道,是为它建造,是让它在上面生死轮回的, “去做一个大床,实际是在玩弄它。”他说道。只有用微观的眼光去感知它们的世界时,才能够回到生命体平等的初心, “我不要设计,应该是我和蚕结伴而行,需要互动。”展览名称“蚕我,我蚕”便是艺术家 30 余年与蚕共处,共生的最深刻总结。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读老庄以及东西哲学史,梁绍基坦言一开始接触海德格尔的哲学时觉得很晦涩,但在养蚕 30 年后,他还是经常研读,慢慢地懂了,他认为艺术家不是表面觉知的,而是通过在自己的创作中去认知。蚕丝对他而言,就是时间和生命在漫长的旅途中, “存在”以及“存在者”的显像。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白光”便象征着艺术家对于丝的理解, “它是绵延无穷,而且好像是虚空、虚无,很微弱,但是它又无穷地延伸,它是虚灵,有灵性”。 1980 年代末正是科学家们开始关注基因、克隆课题的时间点,关于生命体,科学家在回答,也在研究生命,而最根本的微观世界的源头在哪里?梁绍基则沿着一根丝去追寻。 “当我把干茧定上丝布的时候,阳光透过小窗照进来,它上面有恍恍惚惚的影子,突然想到以前读老子读到的一句‘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我感觉到这里面的朦胧美,诗意,东方的美学观念,而在这种透薄的里面,我感到有一种生命意象,它活了。”
在对自己艺术创作的要求上,梁绍基坦言自己希望从时间和生命的本源开始追问,而不是简单地罗列过往作品,他曾经说,自己的追求,是把“物”变成“道”,对于这两个概念,他解释说,具备很强物质性的装置艺术,包括多媒体艺术、具备科技性的艺术作品,如果不被创作者认识清楚,就不能成为语言,更不能成为概念,也不能成为承载精神性和具备升华空间的艺术品,它还是材料,也仅仅是材料和工具。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能够从形而下转换至形而上,材料,也可以是一个信息,一个观念,材料不应该僵化地被看到,它可能是工业化的产物,化学反应后的产品,但物质本身,以及材料被放置于某种场域里所折射出的精神,是可以玩味的。
“我不是刻意要做一位隐士”
居住于天台数十载,梁绍基说自己并“不是刻意要做一位隐士,而是觉得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回忆起自己在天台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他曾经看到山上一个小寺院里面的一句话:“生命的富足来自于独处,独处意味着当下。”即使你居住在遥远的僻林,你不懂得独处,你不能安住当下,回归当下。
他所认为的艺术家最应该具备的,是真正的回到自己的心的审视态度。 “艺术家应该由自己独立的审视,有自己的语言,有对自己解码的一种方式,而在都市里,却太容易被同化。”他说道。海德格尔所说的“还乡”,在梁绍基眼中,真正的还乡,是回到自己,回到自己的心,回到自己的信念。
冥想,是梁绍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他认为如果仅仅从表面上陈述,很没意思,最主要就是自己懂得。在现在这种都市浮华世界里面自己能够沉下心,冥想其实是一种使你自己能够尽情把外面的污染东西进行清洗的一种方法,是随时的,而不是作为仪式。对艺术家来说冥想还意味着“超越”。天台宗有一个要义,名为“止观”,国清寺的方丈告诉梁绍基, “止观”最终是要回到你的心源,而在“止观”之前的要义是“定慧”,只有“定”,才能生“慧”。
养蚕、识蚕、读蚕的过程,历经了几十年岁月,梁绍基对生命本源的探究和追问,仍在进行,都将有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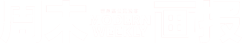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